


如果有一天,你突然能听到一个遥远陌生人的心里话,感觉到Ta所有的情绪,那会有什么事发生?
大年初二(2月2日),电影院空降第九部“春节档电影”。
虽然只是点映,但上座率却非常高,达到21.8%(截至发稿前)。
自从2013年,春节档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第一档期后,就没有电影会选择在这个时间里做点映活动。
这样一部高概念设定下的爱情轻喜剧影片,在春节欢乐的大氛围下,想必会为情侣们带来甜蜜而感动的观影体验。片方和主创想借助这个时机,来测一测它与观众的“通感”距离。
这就是《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》(以下简称《好想》),一部奇幻爱情片,一部适合在情人节看的脱单电影,提前12天,先和观众过过招。

“亲密关系是人和人关系里最丰富却又最复杂的存在,因为人性本就是复杂的,我希望我的爱情故事里人物的层次是丰满的,而不是被标签化的。所以,我们的片子里面,每个人都有值得被理解和从他的角度而言对的东西。”
第一导演特此专访《好想》导演孙琳,才知道,电影里的爱情和奇幻都只是一个引子,她还要讨论人的终极哲学,关乎我们每个人未来的模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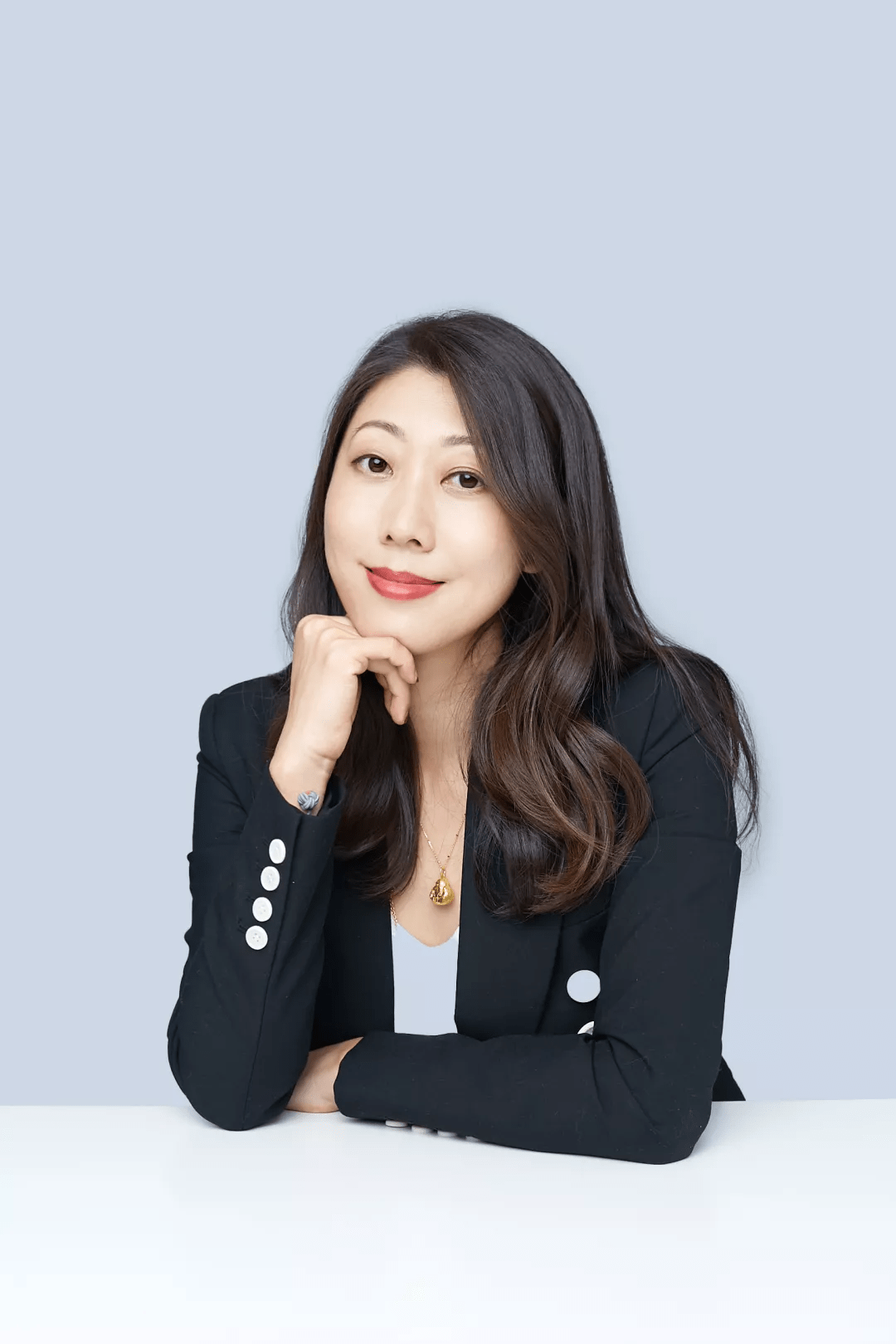 导演孙琳
导演孙琳
看《好想》这部电影,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——通感。
在语文课堂上,老师会说,通感是一种修辞格式,它是把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等感官,遣词造句,连接转换,比方说,这红色真暖,这香气如歌声般动听。
但在《好想》的世界观设定里,通感是指人与人之间精神感受的超现实连接。
故事中,一对分隔在地球两端的青年男女,因为女主角某天摔了一跤,磕“坏”了脑袋,导致与遥远的男主角产生脑波回路——我说的话,你能听到,你的情绪,我也能感受到——两个人因为彼此感知互通,大脑里多了一个“你”,生活顿时乱作一团。
导演孙琳解释说,“奇幻在这部电影里并不是要‘飞’,它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形式。”比如在电影里,女生作为初级社畜,被领导骂得好惨,特别委屈地哭了,而男孩突然在此刻感同身受地悲伤起来,也跟着流了泪。
更有趣的是,当男女其中一方的心率超过100的时候,还可以对对方形成“远程操控”,比如说,男孩钢琴很厉害,他通过提高自己的心率,帮助女孩在公司众人面前大显神威,击败了女孩的竞争对手,观众由此得到巨大爽感。
作为情感上的“回报”,女孩鼓励这遥远一方的男孩,把一个听诊器放在自己心脏的部位,男孩那边就能听到女孩巨大的心跳声,这种设定给了那个男孩一个鼓励,而那个孤独的男孩,人生就差这一点鼓励,由此,孤独被打破了,两个人产生了情感。

“奇幻实质上是创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假设和探索,是我们心中对理想的自我、理想的人际关系的畅想和认知,是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。”
孙琳导演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创作方向,她给自己年轻的编剧团队定下了世界观、价值观和整体戏剧框架,故事从一个欢喜冤家开写,一直到双方为彼此注入了感情,再到第三幕,这种“超能力”所带来的负能量和误解,直至最终解决情感关系。
男女主人公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同一空间里,但命运不断周旋,蝴蝶效应加剧,爱情紧紧相连。
导演坦言,恰恰是走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,才会有这种故事的讲述,“我是70后,现在来解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话,可能角度跟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样。这两三年我一直在探索孤独与懂得的关系,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能懂你。我们电影里有一段话,在你的世界里,70%的人只是认识你,20%的人只是想利用你,6%的人讨厌你,4%的人喜欢你,只有0.1%的人懂你。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太难了,所以我们时常会感到孤独。”
实际上,把《好想》女主角和男主角前后加在一起,也就是导演孙琳本尊,“我26岁之前就是女主角安易,26岁之后就是男主角高昂。”
“我大学毕业后上了三年班,参与了国内很牛的时尚杂志的创刊,别人眼里觉得我很光鲜,但实际上所要面对的跟每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,”《好想》里女主角安易被领导甩脸的情节,就是导演孙琳的亲身经历,“当时我在一家商场里给客户看为其拍摄的杂志大片,客户不满意,当着众人面把大片全扔到我身上了,我当时就哭得不行不行的。”
 安易(周依然 饰)
安易(周依然 饰)
当然,真正的心结还是梦想的未竟。于是孙琳在领导万般不解之下毅然辞职,扭头考上了北电的电影学系研究生,但却在北电毕业后艰难磨合事业,没有机会做导演,做自己的表达,这就又成了《好想》里男主角高昂的状态。
电影里有一个道具,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按照导演孙琳的解释,这是男女主角两个人的一个共同支点,“你肯定知道毛姆的人生观是什么,就是我要月亮还是要六便士?高昂就像毛姆一样,是孜孜不倦、百般辛苦的追梦者,落魄到去小教堂里做调音师,但女主安易就像大多数人一样,遵循世俗的标准,不太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
 高昂(施柏宇 饰)
高昂(施柏宇 饰)
一开始编剧团队担心建筑师、调音师可能不太落地,孙琳却有自己的见解,“有人见过皇上吗?见过太监吗?为什么我们却还能懂他们的情感?是因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职业身份,你的内在的情感困境跟观众是一致的,能跟他们共鸣就OK了,对不对?”
相反,真正不OK的,也是真正激发孙琳的表达欲的,恰恰是当下青年人的“社交分裂”属性。
在导演看来,我们当今的社交模式正在重组裂变,朋友圈,微博,短视频,当下的信息截取方式便捷了,交流的成本也低了,但实际上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更焦虑了,更不确信,更不安了,内心都是悬浮的。
“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麻烦的,特别棘手的事——年轻人连恋爱都不想谈了!”这可能是源于日本流行过来的低欲望文化,这种现象正在蔓延。
“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片名《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》中的那个‘去’字,而不是说好想跟你“来”一场异地恋或网恋,因为你们一定要见面,我们电影海报的slogan就是‘我们见面吧’,这是我潜意识层面最渴望的最终人际关系,真正的亲密关系,当下来看是一种畅想。”
聊到这里,《好想》这部电影可以试图进入到一个更潜在的哲学谈论,那就是,人到底有没有办法了解彼此,了解自己。
就连去年日本本土电影票房冠军《新世纪福音战士新剧场版:终》,这套影响了整个日本动漫行业的跨世纪作品的终结作,都在对“人与人到底能否做到绝对意义的沟通”做出回答——只要你愿意,你能。
但在大部分的作者电影创作里,这是误解,这没有答案。
孙琳导演给出了一个答案,人的终极命题,可以靠面对面的沟通来化解。
 导演孙琳
导演孙琳
在导演孙琳的脑海里,一直有七七八八个故事,每一个故事,都有同一个母题——人与人的关系。
“我平时会很留意这些表达,比如说出去喝个咖啡,我都会猜,对面坐的这一对是什么关系?那三个人又什么关系?”
之所以对此敏感,跟导演儿时经历有关系,“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,总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,我就在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我不希望它是恶意的,我希望彼此都能特别理解对方,我内心是有这么一个愿景的。”
尤其是在疫情之后,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都变了,我们不再能随意见面,“卡夫卡说过一句话,难道现在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书信交流吗?他的意思是,不见面的这种交流是无效的,书信是在跟幽灵交流。”
当下,人类已经完全进入这个数字幽灵时代,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,人际关系在逐步丧失,这让导演孙琳特别的心痛,“在我这儿其实挺悲观的,人际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了。”
所以,要想通过导演的身份一步步做自我表达,就要先把《好想》这个通感爱情轻喜剧影片端上台面,因为在所有的讲述办法中,这部电影最容易和类型挂钩,80%的笔墨是爱情,而另外20%才是社交哲学。
“如果《好想》的想法从我脑子里产生开始算的话,是两三年前的事,但真正落实,到最后把它拍出来,差不多就一年。”
拍摄不也是一种“顺势而为”的社交与沟通吗?特别是面对演员,谈到周依然,导演描述到,她的共情能力特别强,遇到一个表演要求,她的心还是自己,外壳马上变成主人公了,有一定的职业的表演理智。但施柏宇又是另外一个感觉,施柏宇是心和躯壳全变成了那个人了。这时候,就需要导演来“解救”,我得把他掰开了揉碎了,让他挖掘一下他自己的故事,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一点,但一旦他变成那个人的时候,他真的就是那个人了,踏踏实实就是他了。
当然,导演这么做还有一个终极目的,就是尽可能,拓宽国产爱情片的多元表达。

再说回到大银幕。
长久以来,国产爱情片的核心都是青春疼痛,无论是IP改编还是原创,都让爱情片变得局促,不多元。
对于一个创作者,《好想》这部戏,孙琳导演也好想给爱情片再拓宽一个赛道。
“亲密关系是人和人关系里最丰富却又最复杂的存在,因为人性本就是复杂的,我希望我的爱情故事里人物的层次是丰满的,而不是被标签化的。所以,我们的片子里面,每个人都有值得被理解和从他的角度而言对的东西。”
按照孙琳导演的理念,就是一句话——我们不要推倒人性。
“这次《好想》的发行方决定在春节档做点映,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,如果我的表达能让大家早点看到,尤其是今年春节档也没有爱情片类型,可能有一些情侣人群,或者是不得不在两地过年的异地情侣确实有这样的类型观影需求,那也是多了一个选择,可以早点听听观众和市场的意见也是好的。”
当然也会紧张,导演自己也很坦诚,说没有顾虑、毫不焦虑那是假的,但创作成果早晚是需要大众检验的,她至少能让自己非常平和地跳出来去看这件事。
类型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?一部爱情类型片的意义又是什么?它至少能在生理上促进你平常或者近期没有得到的感知,在获得了这个信号之后,这部电影的使命就结束了,接下来,就要看你是否携带这个功效,回归现实生活。
“是这样的,一想到爱情片里接吻那一瞬间,能焕发起他疏离的本能,我就很开心。”
《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》已开启全国点映,并将在2月14日情人节正式上映。

猫影开放接口API
9667资讯2025-01-18
猫影完整应用安装指引
7378资讯2025-01-19
猫影公告必看
6449资讯2025-01-19
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详情一览
2871资讯2025-01-19
从周润发的大哥,到客串《乡村爱情》,他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了
2713资讯2025-01-19中国将拍真人版《银河英雄传说》 计划拍摄三部曲 2020年首部曲公映
2699资讯2025-01-19
吴京和樊亦敏相恋,樊亦敏却转身背叛了吴京,而如今的吴京却是她高攀不起的。
2682资讯2025-01-19
华晨宇和谢霆锋再次同框后,观众明白他二人的相遇,真好
2672资讯2025-01-19
因为害怕番位引战,《雪中悍刀行》的幕后人员竟把事情做到这份上
2553资讯2025-01-19
他们饰演了母子后,却在现实结婚了,如今35岁双胞胎儿子超可爱
2454资讯2025-01-19